
时间:2021-09-07 09:22:25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9月6日电 题:杨立华:如何看待“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
作者 李晗雪 刘玥晴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学术架构也在与西方近现代学术的相遇中,遭遇外界与自我双重的审视和反思。“中国有没有哲学?”正是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讨论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用和西方哲学家不同的方式述说主张,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性格及其在今日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问“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是如何开始的?对此,中外学界产生过哪些重要的正反面看法?
杨立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其实从“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出现时就有。“哲学”这个学科的名字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中文本身没有“philosophy”的对应词汇。日本有位叫西周的学者,是最早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的;后来“哲学”被转介到中文世界里,用它来指称中国的根源性思想。
“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写作随之逐渐展开。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哲学系,当时名称是“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其中设有“中国哲学门”。冯友兰先生等是中国哲学门的第一届学生。
当时是陈黻宸先生讲课,胡适回来之后,又有了新的讲法。陈先生是从上古讲起的,据记载,他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而胡适从老子开始讲,他引入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史的方法。后来胡适很快就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但是只写完了上册,下册没有再写,因为他的心思变了——他开始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所以后来他基本不再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只有上册。
但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两卷本里讲:“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如培根所说。研究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研究其哲学,则对于其时代其民族,必难有彻底的了解。”在冯先生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精华。所以当然要强调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受质疑,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人继续质疑、讨论。近20年中,对“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2000年左右。这个讨论怎么起来的?有几个背景:
第一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整个20世纪,在欧美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居主流。相当一部分分析哲学研究者或者分析哲学家倾向于把其他哲学都贬低为不是哲学,这在20世纪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即使如此,分析哲学也不能占领整个哲学的场域,因为哲学的脉络里显然还有欧陆哲学的传统。比如按分析哲学的说法,黑格尔是不是哲学家呢?
另一个背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一个文明高度的问题。有一部分学者否定中国哲学是要否定我们这个文明的高度,也就是认为中国文明没有根源性的思考,或者说无法证明存在这样的思考。从文明论的背景来说,中国有无哲学就是一个必须回应的问题了。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逐渐居于优势地位,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把别的民族、别的文明贬低为次等级的文明,甚至是不文明。19世纪末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里,就显现出一个非常强的文明论传统,即认为西方文明是最高等级的,而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是低级的。这个心态也可以说是“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背后的焦点。虽然这话很多人并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从根本上要否定中国文明高度的。
以上是我认为“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出现的背景的线索。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较起真来,“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得先有一个标准形态的哲学,才能这么问。要是有这样一种思想形态叫哲学,并且是唯一的,而且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发现不了这种形态的思想,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但是西方哲学传统里有标准形态的哲学吗?没有,到今天都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有无哲学”根本上是个假问题。
另外一点,他们认为中国哲学不思辨、不论证,所以哲学品格比较弱。而我们自己的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也用“境界”“精神形态”这样一些含糊其辞的说法来讲中国哲学,等于在某种意义上配合了上述说法。不思辨、不论证怎么会是哲学?就说先秦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哲学史上要面对的、提出的重要哲学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都被提出,并且被以理性的、思辨的方式加以思考、论证和辩论。中国的哲学家在证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时候,往往并没有采用严格的论证形式,但实际上是有自己论证的理路的。
其实还有一个误区是大家以为西方哲学是在“论证”,但认真去看西方哲学史,有几个真正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论证?又有几个哲学家提出的观点是按严格的形式论证的方式得来的?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人云亦云,只是一种印象式的概括,而且西方哲学里还有大量象征性的说法,比如著名的“流溢说”。
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争论的背景分析,刚才谈到了哲学内部的倾向问题、文明论的问题,以及有无标准哲学形态的问题和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对中国哲学的误解。我这些年着力在校正这类误解,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论证以新的形态写出来。
中新社记者:您自己会如何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
杨立华:中国当然有根源性的思考,除非是眼睛出了问题,否则怎么会看不到呢?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根源性的思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这不也是对万物本根的思考吗?《孟子》里“尽心知性”章,不都是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思考吗?《墨辨》里的光学、几何学、逻辑学要素是多么发达!这个世界有一批人是不听道理的,说什么都没有用,比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低等级的文明。有人问我中西交流的问题、怎么去给西方讲,我说不用跟他们讲什么,某一天他们想学中文了自然就学了。
“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提出,尤其是在中国学界内部的提出,并且产生那么大争议,那么一大批学者要顽固地把中国思想贬低为非哲学,背后因素不是偶然的。当他们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显然不是认为哲学是不好的,他们认为哲学是好的,所以中国一定“不能有”。就像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科学是好的,中国一定不会有。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么低等级的文明就不会有哲学。但是我会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有理说理。我只用“中国哲学”“孔子哲学”,尽量不用“孔子思想”这样的词。孔子当然是有思想的,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态。

中新社记者:今天,中国一些经典哲学思想是如何体现在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的?
杨立华:到处都是。我这几年常有一个讲法:我们的中国精神,就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塑造的。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离我们都不远,像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这样的人和他们的思想,就在我们语言的根基处、在我们思想的根基处、在我们感受世界方式的根基处、在我们实践结构的根基处。我们日常生活里随便一个举止、习惯里,都有孔子。比如中国人习惯于储蓄,孔子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对世界根本的理解——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单向地向好,这个世界起起伏伏,我们的人生也起起伏伏,即使我们处在比较好的阶段,也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好而做准备。
中国的这种此世性格的文明,使得我们中国人根底上看待世界的方式跟别人不同。我在《此世品格与知止的文明》这篇文章里对此有明确的论述。
虽然一代人与一代人不一样,但无论怎么变,只要汉语在,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就在;汉语在,中国品格就在;汉语经典在,中国思想、中国的根就在,就会塑造一代代人。不管家庭结构,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新的形态的变化,那个基本价值都在,即中国文明的此世性格和以此世性格为基础的知止精神。
此世性格是中国哲学品格的根底。哲学、一般性的思想、宗教、艺术……中国文明的一切方面都体现出非常强的此世性格。“此世”对“彼岸”,我们这个文明不是以彼岸为追求的。当一个文明以彼岸为追求的时候,“此世”总体上被视为缺陷。如果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此世的不满足,投射到一个虚幻的影子上去、把那个东西叫做彼岸,并以彼岸为目标,那么此世就是过程,是要被克服和超越的。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文明根底是:此世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过程。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和哲学目光。因为彼岸需要太多假设,而此世是直接呈现的,所以中国哲学有个特别根本的性格——此世性格。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根本目光是最少假设的,没有那么多虚构,我们不用虚构原罪、上帝创世、天堂地狱、末日审判、伊甸园,这些虚构我们都没有。所以中国哲学的表达总是简洁的,所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中新社记者: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也开始使用许多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那么您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应该怎样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赋予中国哲学新的生命力?
杨立华:我有这样一个态度:在汉语中思考。所谓在汉语中思考,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中国哲学概念,也没有纯粹的西方哲学概念,它们都已经进入到现代汉语世界中。时代的语言构成思考的边界,一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尝试去拓宽、或者至少是充分实现这个时代语言的可能性、思考的可能性。举个例子,“理所当然”这个词里还保留着两宋时期儒家哲学的讲法,一旦说“理所当然”,那就是“必然”,在宋明理学背景里,“当然”和“必然”是统一的。但我们今天谈的“当然”和“必然”,是不统一的。这其实就是西方哲学对我们的语言概念的影响了。所以我们重新谈论“当然”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时,既不可能撇开中国固有的脉络,也不可能撇开已经浸透了的西方思想传统。
当代的学者应该诚实地面对学术、面对知识、面对真理。哲学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其实不是如何去跟其他的学术界交流或者获得国际的认可,而是真实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环境、思想环境、语言环境的整体土壤里思考,尽可能获得对时代有力量的、扎根于中国古代、有足够广阔的现代视野的一种新的哲学探索形态。世界上各种主要文明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翻译进汉语,现代汉语的土壤已经足够好了,我们缺的其实是种子。(完)
【受访者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1971年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大庆市五十六中学毕业。浙江大学工学学士(1992年),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8年)。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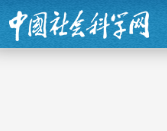
“十五五”中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条主线
2025-11-05
新华社:在关税逆风中艰难前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辨析
2025-08-20
东西问丨肖世杰:中国法治文明经验如何为发展中国家人权治理提供借鉴?
2025-07-29
东西问丨宋海涛:国际合作为何是人工智能时代“鲜明底色”?
2025-07-27
东西问丨王文:为什么中拉人权合作越来越重要?
2025-07-26
东西问|尼古拉斯·斯特恩:中欧如何加强气候治理合作?
2025-07-22
东西问|刘进田:中华文明的人权潜能及其世界意义
2025-07-20
东西问丨葡萄牙“中国观察”智库主席鲁翊君:缘起“丝绸之路” 架葡中合作之桥
2025-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