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8-05-21 10:57:21来源: 意大利侨网
但要是参照一下这二位的著作在中英文之间被翻译的状况,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巨大的“逆差”就出现了: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作品问世20年,即已进入中国内地17载,简体中文版行销数千万册;而在华人世界风靡超过一甲子、销售超亿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却只有区区三部五卷由香港的出版社出过英译本,在英语世界中可说默默无闻。
这般“遇冷”在中国当代畅销书作家身上并不罕见,例如另一位拥有无数华人拥趸的女作家三毛,即使她曾长期居留在西班牙,并以生花妙笔遍写当地风物、“启蒙”了无数中国人“西游”,但其作长期没有西班牙译本,其人也不为当地人所识……
而如今情况似乎正在悄悄改变。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历经5年严谨的版权引进和翻译编著过程,今年2月,以出版优秀译作著称的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雄诞生》。这是该部金庸经典作品首次被译成英文出版,问世不足3个月,已加印超过7次,受到市场大力追捧。
出版社还宣布,将用12年时间,以一年一卷的速度,完整出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金庸作品。英国小说家Marcel Theroux在《卫报》上刊发评论说:“我不由得感叹,自己五十多岁才接触这本小说,它可引发一辈子对中华历史与文明的狂热兴趣。”
主持该出版社的英国著名图书推手Chrisopher MacLehose说:“我相信英美的读者终有一天,会跟我们一样读到金庸的魔力。可能不在一时三刻,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无独有偶,在欧洲大陆另一侧的西班牙,RATA出版社自2016年开始推出中国传奇女作家三毛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两种译本,翌年又有《温柔的夜》译本面世,市场反响热烈,如今第三本也正在紧张翻译过程中。
近日,在不同的文化活动中,羊城晚报记者巧遇了上述事件的两位关键人物:刚译完“射雕”第二卷的香港译者张菁,以及三毛作品的译者、西班牙女郎董琳娜(IRENE TOR CARROGGIO)。
听她们聊起自身的经历、体会,记者深感,这一轮英译华语文学畅销作品的热潮,不仅与中国崛起后西方读者对当代中国作品的阅读兴趣猛增有关,也得益于更多修习汉语的西方青年、更多谙熟西方生活的中国文化人出现。他们投身翻译大潮,没有过多传统文化的包袱,而是以新的立场、视角和资源,做出与传统翻译家们不同的尝试。这一番作为,让西方读者在已知《论语》《道德经》和《红楼梦》等中华经典之余,也开始了解金庸、三毛这些已成当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文学符号。
张菁:金庸作品译者
上月底举行的“2018广州保护著作权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承办单位是朗声图书,他们因拥有金庸作品中文简体字版独家版权而声名大噪。活动上,他们请来《射雕英雄传》的英文译者张菁助阵,给好奇的中国“金迷”,也给羊城晚报记者一个机会,了解武侠经典走向世界的过程。
张菁成长于香港,一直接受良好的中英文教育,虽然读女校,但性格爽朗的她从少年时起便迷上了金庸的武侠世界,“那时候,向往行侠仗义、特立独行的酷女孩才最时尚,金庸当然是必修课!”但后来她继续到国外攻读艺术史专业,并留在英国从事博物馆工作,兼做戏剧翻译、中西艺术文化交流等工作,虽然真正是闯荡世界了,却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金庸作品走入英语世界的“推手”。
张菁与另一位瑞典姑娘安娜·霍姆伍德(中文名“郝玉青”)是“老相识”,她们在英国伦敦圈里是知名的中英文译者,也是朋友,还一同翻译过台湾的文学作品。郝玉青同时也是一位图书经纪人,当她发现金庸著作在英文图书中的空白,便迅速开始了“补白”的工作。2015年,郝玉青翻译“射雕”第一卷已近尾声,决定邀请张菁给她接力。
如今,“射雕”英译本的第一卷已经出版并大受好评,张菁翻译的第二卷也已交稿,预计明年上市。金庸先生绚烂雄奇的武侠世界,正由两位“80后”的女译家向西方读者徐徐拉开大幕。
“射雕”英译本第一卷,书名《英雄诞生》

羊城晚报:安娜邀请你参加“射雕”的翻译,你有没有犹豫?
张菁:没有,我几乎是立即答应了。中国人谁不知道金庸呢,我本来就做翻译工作,又从小看他的武侠小说,能把金大侠介绍到英国,简直太兴奋了!
羊城晚报:这部书四卷一百多万字,你们二位如何分工?
张菁:我加入的时候,安娜已经把第一本的主体翻译好了,对我来说首要是延续她的文风,同时结合第二卷及后文的内容,跟她讨论、打磨许多基本概念和提法。我在上海,她在英国,每天都不停地联系。等我翻译的样章获得出版商通过,我们俩的分工也定下来了,安娜翻译第一、第三卷,我翻译第二、第四卷。
羊城晚报:已推出的第一卷英文书名是《A Hero Born》(《英雄诞生》),那你的第二卷译本目前情况如何?
张菁:我从2015开始,用了两年多,直到今年春节后才将第二卷全部交稿。书名是《A Bond Undone》,中文名还没有定,计划明年初发行。
羊城晚报:武侠小说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类型文学,有一整套我们中国人已经约定俗成、可外国读者却难以意会言传的概念,比如江湖、武林、侠等……要如何翻译?
张菁:对此安娜已经在全书的引言里做了一些界定,比如“江湖”(rivers and lakes)是个象征性的地域,包括“武林”(martial forest)和按某种道德方式、伦理规矩生活在其中的“侠”(xia)。这是一套特殊的语言体系,读者也要慢慢完成转换。
有时直译、有时音译,尽量把中文的用意和快感传达到西方
羊城晚报:这可能也是广大“金迷”们最关心的问题,金庸世界里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招数、含蕴隽永的人名,要怎么翻译才能传神?
张菁:这真是一言难尽!这些专门的“金式语言”,要根据在小说中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来翻,有时直译、有时音译,又或者结合起来(例如“九阴白骨爪”译为Nine Yin Skeleton Claw,“阴”就音译为Yin,而这一招最突出的展示是骷髅头盖骨上能正好插入五个手指的五个洞,所以我们用骷髅skeleton代替白骨bone),反正要尽量把中文的用意和快感传达到西方。
在人名方面,像丘处机是历史人物,就用了音译;网友说的“Double Sun”,我们是把它作为“王重阳”的别号来用,有些章节里我们同样会用“Wang Chongyang”的拼音。还有像陈玄风、梅超风等,他们是大恶人,名字中都有一个“风”字,我们就用英语当中表达不同种类的“风”的词给他们师兄妹命名,梅超风是Cyclone(暴风) Mei,陈玄风是Hurricane(飓风)Chen等,表现一种破坏性。在第二卷中他们的其他同门都出来了,我也都根据英文中表达不同的风的单词来命名。
羊城晚报:你们翻译的宗旨是什么?
张菁:阅读的快感,让读者一直想看下去。金庸的故事本来就是好玩的,如果死抠字眼让文字沉闷繁琐,反倒不美。所以即使是金庸半文半白的语言,我们也要考虑平衡表达,要让英文也能活起来。
羊城晚报:你觉得翻译金庸作品最难处在哪里?
张菁:其实还不在于给武功或侠客命名,而是如何把他们比武、练功的全过程翻译得行云流水,又能表现东方的武学精神。我练了一年多太极拳,当然这首先是对我长期伏案后糟糕的颈椎有帮助,然后也让我对武功的翻译有了一些新感觉。比如高手过招时,常会有“胸口一缩”的形容,以前我就是按动作直译的,现在师傅一解释,我才明白了这是在形容有功夫的人借力、卸力,其实也隐含着以柔克刚的意思。
另外,其实有些角色的感情处理是很中国式的,要让西方读者明白也很难。例如,杨康和穆念慈的感情,篇幅很少,但很重要。我们中国读者很懂这种含蓄的爱情,但试读时西方读者就不明白,他俩情感如何产生和递进的。第二卷中杨穆爱情的发展对于主题很重要,但我又不能加他们的戏份,只能在有限的场景里增加情感浓度,这也是一种再创作。
这一次译本能成功,因为“天时”到了
羊城晚报:我们知道,中国国学经典大都有精良的英文译本,例如《论语》已有超过60种英译本!可是金庸作品作为华语世界里的“现象级”畅销书,之前却译本寥寥,在西方读者中“水土不服”。那这一次你们的译本为何能成功呢?
张菁:这还真不是以前的译本或出版社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天时”到了。老实讲,我们都在享受中国国力强大的成果。十多年前,我在伦敦V&A博物馆工作,那时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兴趣虽有提升,最多也就停留在艺术品层面,那是不需要掌握中文或中国文化也多少能欣赏到一些的。北京奥运会之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贸易的发展,甚至普通人的生计都在向中国靠拢,简单说,中国的图书很多人想看了。
另一方面,在人们的阅读习惯上,长篇奇幻、网络小说等大体量小说也在这段时间流行起来,像《魔戒》《哈利·波特》《权力的游戏》等等,动辄几十册、上百万字,这也改变了西方读者的口味。以前中国人看十卷的流行作品不出奇,但西方读者很难,现在出版潮流、阅读习惯的改变也让他们做好了准备。
翻译“射雕”,首先它是一本小说,不能太严肃,不能一开始就筑起高墙,不能让读者一看丧失“食欲”。要先把他们领进门再说,慢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所以我们要忠实于读者,强调小说的追看性。
羊城晚报:但也有人对你们的译本有些不同意见,比如没有一字一句全都翻译出来,像原著第一章说书人交代宋高宗昏庸、岳飞遭秦桧陷害的大段历史背景,在英译本中就缩短了很多。
张菁:是的,这其中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西方读者并非现成的“金迷”,他们翻开书之前对中国历史、对武侠文化可能一无所知,译本要先吊起他们的胃口。试想,如果打开书就发现是大段的注解和历史陈述,还看得下去吗?读者不想看,也就谈不上熟悉和爱上这个江湖,或了解中国历史了。
羊城晚报:但我们如此热爱这作家的作品,恨不得每一根毫毛都要体现在译本中。
张菁:我做翻译,希望吸引的读者不是这些已有的“金迷”,而是不会中文、本来对中国不了解也谈不上喜欢的人;我要“招惹”的,不是那些会自己“埋位”的客人,而是本来不会自己走过来的陌生顾客。像倒模一样直接复制,不可能达到文化传播的最大化。
董琳娜:三毛作品译者

上月,浙江舟山作为女作家三毛的祖籍地,启动第二届“三毛散文奖”评选并举办文学纪念活动,请来了董琳娜作为嘉宾。2016年秋天,董琳娜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又和Sara rovira教授合译了加泰罗尼亚语版;2017年秋天,由她翻译的三毛《梦中的橄榄树》出版;今年秋天,她将交出第三部三毛作品译稿。
27岁的董琳娜学习中文十年,口语水平之高,足以用“谈笑风生”来形容。“直到今天,我还会在早上起床时,忽然问自己,真的是我吗?我翻译了三毛的作品吗?”言语间流露出顽皮的欣喜,青春洋溢。
西班牙读者对三毛一无所知
董琳娜对于三毛的认识,来自中文老师布置的一项作业:找一个中国人问问,为什么学习西班牙语?——毫无悬念的,她找到的留学生回答,是因为女作家三毛。
从此,这位中国女作家在她心里扎下了根。董琳娜很意外,与西班牙渊源深厚的三毛,曾这样深情描述过加纳利群岛——“这儿有我深爱的海洋,有荒野,有大风,撒哈拉就在对岸,荷西的坟在邻岛,小镇已是熟悉,大城五光十色,家里满满的书籍和盆景,虽是一个人,其实它仍是我的家”——可她的作品竟然从未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普通西班牙读者也对她一无所知。

《撒哈拉的故事》西班牙语译本成为畅销图书
完成了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专业的学习之后,董琳娜决定到中国继续学习,心里藏着一个夙愿:等到自己中文水平能够胜任,要将三毛的作品翻译到西班牙。
她先到黑龙江大学读语言生的课程,第一篇课文竟然就是三毛《沙漠中的饭店》!“我又一次遇到了她,缘分啊!”于是她开始将三毛的三四篇故事翻译成西班牙语,寄给西班牙的一些出版社。然而,接下来三年,并没有任何回音。
直到2015年,已在上海财经大学读研究生的董琳娜突然接到来自西班牙RATA出版社的电话。这是一家新出版社,致力于发掘那些“由心写作的作家”。出版社的一位懂中文的编辑向社长约兰达·巴塔耶推荐了三毛。约兰达读着样章爱不释手,认定三毛是一位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这正是出版社选择作家的宗旨。
“三毛鼓励了我。”董琳娜刚开始时觉得三毛的作品较浅显,但随着翻译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古文典故和中西文化理解的差异出现,使她不断扩大自己查阅资料和请教的范围。经过6个月“边学习、边译稿”的紧张工作,董琳娜将《撒哈拉的故事》交稿。RATA出版社很珍惜这个项目,不仅约兰达亲赴台湾面见三毛的家人,而且在社交媒体、西班牙的各种媒体上宣传新书。这是当地读者第一次直接读到三毛作品,《撒哈拉的故事》迅速成为当年出版社卖得最好的图书。
三毛的丈夫荷西是真实存在的
三毛与西班牙丈夫“大胡子荷西”的浪漫恋情,一直是她作品中最动人的片段,但因为时间和地域的久远阻隔,也曾有过一些不同声音,怀疑这个人物是作家“艺术加工”的结果,甚至还不止一次有人远赴当年三毛和荷西居住、游历的地方,希望能证实行迹。对此,董琳娜斩钉截铁地说:“三毛的丈夫荷西是真实存在的!我和他的家人有过很多接触,他们能理解三毛。”
董琳娜说,三毛作品中提到过很多荷西的亲友,但都将名字写为汉语的,所以她最初联系荷西的家人,是为了准确转译这些人物的西班牙名字。“后来我们谈得越来越多,我感觉,虽然他们之前并没有看过三毛的作品,但现在了解到,也觉得很有意思。”荷西的父母都已去世,董琳娜联络较多的是他的姐姐们。“我知道,其实她们看这些作品也会有一些不适,因为三毛与荷西家人的相处中并非只有笑声。而且,有时当事人会有不同版本。例如,看到《撒哈拉的故事》中那篇《亲爱的婆婆大人》就会有点尴尬,不大明白为何三毛将婆婆描写为‘假想敌’。”
但董琳娜再三强调,她很感激荷西的家人,他们从未干涉或反对过三毛作品的内容,而且对翻译提供了很多无私帮助。他们理解,这是文学作品,三毛是作家。
如今,董琳娜获得了奖学金,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继续攻读影视翻译专业的博士,同时着手第三部三毛作品的翻译。这一次,她打算不再沿用三毛华语作品的现有结集,而是选取作家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品,描出一条“轨迹”。出版社经常会转来热情的西班牙读者邮件,推特上也常有话题讨论,前两部作品依然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大书店里畅销——这一切让年轻的董琳娜很有成就感。
董琳娜说,西班牙国内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还多数是关于《论语》或者《红楼梦》,“都是老先生的作品”,她开了个玩笑。董琳娜喜欢的却是余华、张爱玲等,所以下一步她希望能推荐更新、更有意思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女性作家,例如我最近关注到的颜歌。”(羊城晚报)

“十四五”福建文化强省建设的多维观察
2026-01-24
浙通四海!“Touch Zhejiang·Walk China”国际青年年度交流分享活动举行
2026-01-2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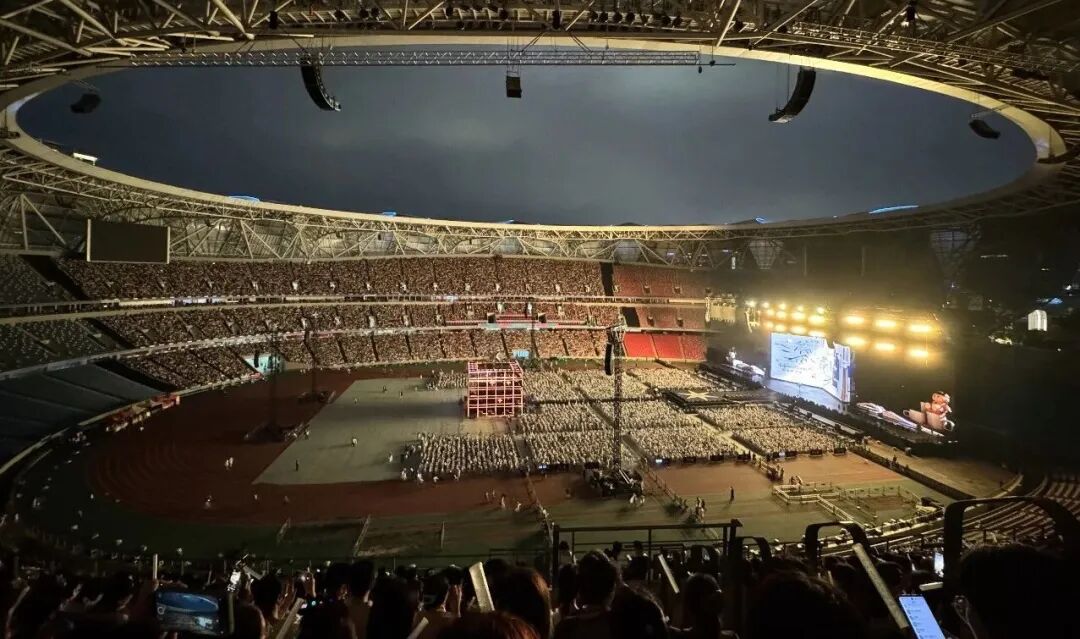
最高奖励100万元!浙江出台细则,支持举办演唱会、音乐节等
2026-01-23
“大师足迹 奋斗赞歌——张文新艺术回顾展”在韩玉臣美术馆启幕
2026-01-20
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教育部等7部门发文
2026-01-19
【学习规划建议每日问答】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把握哪些重点
2026-01-13
CMG svela il promo per il Gala della Festa di Primavera 2026
2026-01-12
从“文化”到“文化体系”——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一笔
2026-01-12